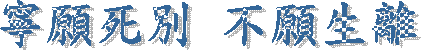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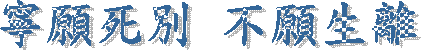
![]()
人到中年,再不是年少時的心境,更不是幼年時的懵懂。
我對一個美國幽默影集中的片段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有一個小女孩,養了一尾金魚。她每天望著魚缸,看著金魚慢慢的長大,對著牠說話。有一天小女孩的父親發現魚死了,非常擔心女兒接受不了,想著要怎麼向她解釋「死亡」,也想藉這個機會給女兒上一堂課,讓她對人世間如何為故去的人辦後事建立一個概念。原本這父親甚至想到要為這尾金魚舉行一個喪禮,埋在院中,是女孩的母親反對,認為太過,於是決定沖入馬桶;可是在沖水之前還是不免對女兒說了一大套的道理。說著說著眼看小女兒的表情越來越痛苦,父親心中非常不忍,正要把女兒摟進懷裡好好安撫一番,卻聞嬌聲稚語:「爸!能快點嗎?我要上廁所呢!」
每次在新聞中看到比方有哪一位年輕的警察殉職了,留下白髮爹娘、年輕的妻子與年幼的子女,畫面上總是老者與寡婦哭天喊地,悲不可抑,但稚齡的孩子還在一旁嬉戲。這種對比給我的感受往往是:孩子失去至親,是不幸;但發生在還不懂人間悲苦的時候,也是幸啊!在他的一生中,少了一次大慟啊!
我出生時,祖輩中祖父、外祖母都不在了。祖母由於兩岸相隔,始終無緣相見,唯一見到的就是外公。我的外公活到九三高齡,所以我在人生中第一次面臨親人的喪禮時已經很大了。外公與我的年歲相差太遠,他老人家對我這個小外孫女並沒有太深的感情,最後甚至認不得我了。而印象中舅舅與母親等對外公故去的悲傷好像也不是太深,因為畢竟是高壽吧。對外公的故去,我除了知道了喪事的一些規矩外沒有什麼感想,此後的若干年,我對「死亡」的認知也很有限。二十三歲那年自己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知道人在呼吸和心跳都停止的時候其實真的是啥也沒有的,無所謂怕不怕的。可是人生最難參透的可能並不在於自己的生死,「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恐怕才是更費思量的。
我覺得自己對「死亡」這個課題有較深刻的體認,是在最近幾年。每個人都一樣的,到了中年,自然要面對比自己長一輩的人逐漸凋零的現實。每過一年,發生的頻率越是高得驚人!數一數老照片中的長者,一位一位,真似排著隊,當合影中陽世間缺席的從少數變成了多數,不由你不接受能照顧自己的人沒剩多少了。長者與自己的感情,有深有淺,當然感情愈深者愈令人難捨,甚至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要面臨他們的大去時,就會在心底開始擔憂:一旦面對,要如何自處。前幾年我曾經鬧過一年的心病,我記得有一天只是我的父母出門和朋友吃一頓晚飯,我竟一個人在家從他們出門一直痛哭到他們回來,我想得很遠很遠,心頭的憂懼在當時病態的心理情況下簡直大到難以承受。真正的死別,對我衝擊最大的當屬在我票戲的歷程中照顧我十四年的李奇峰老師忽然心肌梗塞於睡夢中故去,他走的前一天我夢到他走了,醒過來半天還在冒冷汗,回過神來深自慶幸是場惡夢罷了,卻不想再隔一天惡夢竟真的變成了現實!這件事發生時我的心病已癒,否則如果還在病中,我不知自己會如何地陷於歇斯底里。死別還有兩回經驗令我難忘:其一是送唐鳳樓老師走,送到火化前的一刻,看到薄薄的棺木就要推進去,想到唐老師孤寂一生,無妻無子,那份悲涼越發令人 心酸。另一回則是在北京參加了郭岐山老師的告別式,那是我頭一回在大陸參加喪禮,與台灣的不同,我沒有心理準備是那樣的瞻仰遺容∼不是在棺木之中,感覺那是熟睡中的郭老師;而正由於感覺只是安詳熟睡,心中明白的現實更加催人淚下。
我覺得行喪禮所謂送往生者最後一程,其實對活著的人而言是殘酷的,因為親眼看到遺容,就決定了生者對死者最後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再沒有任何想像的空間。李敖大師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說古代某一妃子自從病後就不讓帝王看自己一眼,為的是不要破壞了帝王心目中對自己完美的印象;他也盛讚台灣的某位知名女作家,在自己知道罹患癌症時,舉行了生前的告別式,不要親友目睹自己他日病重後的容顏,也不要那種悲傷的氣氛,至於死亡,自己從容去面對就可以了 ∼這都是人世間難見的情懷。最近,我在北京,接獲台灣梅派名票、前台灣電視公司國劇節目導播惠伊涵伯伯過世的消息。與惠伯伯結識二十年,曾經也每週在一起聚會吊嗓一次,他對我多年來照顧有加。前半年我明知惠伯伯病重,一直在醫院,心中非常惦念,可是我因為工作及家中特殊的原因,始終沒能去看望一次,其他長輩說心意到了就好,去了惠伯伯也沒有反應。為此我梗梗於懷,十分歉疚。可是這幾日想想,我現在回憶起惠伯伯,還保持一個相當健康愉悅的形貌,我想到初識時自己還在念大學,為廣播節目帶著小錄音機去採訪、想到在師大國語中心教書的前些年,惠伯伯還沒退休,常常一早帶著他固定的早餐∼剛買的肉鬆麵包到我的教室來聊上幾句、想到我每一場的演出,惠伯伯都不缺席、想到票房中他為我操奏二胡...人稱惠伯伯重病後瘦得脫形,今日想來我不曾看到過,反是美的。我又想到自己沒參加周正榮老師的喪禮,但案頭常放著師母贈我的影音紀念光碟,迴盪在我胸中的周老師的形象也始終如舞台上的美好。
曾聽說這麼一個真實的例子:一位中年寡居的婦人在丈夫去世之後,每一頓飯都還在飯桌對面放置一副碗筷,想像著一如往日與丈夫共餐,維持了相當的時日。有一天一位女同事來訪看見了,一把撥開那副碗筷道:「妳這是做什麼?我告訴妳,今天如果先走的是妳,飯桌對面早坐上新的女主人啦!他可不會為妳擺什麼碗筷!別傻啦!」婦人聽了,先愣了半晌,隨即一笑,從此坦然面對現實,安然度著自己幾十年的後半生。這樣的例子,說明了什麼?除了說明男女對情感的態度不同之外,一個重點是:死別,是可以看開的。前面提到「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大的痛苦也會淡去,因為再不會有來自死者半星半點的動靜對生者造成任何新的刺激。死亡,是絕對的結束,它留給生者的痛苦是最劇,卻也是最終的,換言之也是一種解脫。活著的人對故去的人追憶懷想,所有憑藉的資源就是那麼多了,不會再增加了,不會再累積了,倒是慢慢慢慢,沉殿了、過濾了、越來越簡化了、越來越精質化了、也越來越模糊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到六個月,生者可以慢慢由苦痛中掙脫,回到一個正常的生活軌道中。
但是,人生要面對的另一個課題「生離」呢?與「死別」相較之下又如何呢?
理論上說,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還有希望;但事實上很多事不是如此的。我的父親在十九歲的時候隻身離開老家安徽到了台灣,我的祖母在老家盼再見獨子一面盼到眼睛哭瞎了都沒能如願。我一直記得一天我放學和平時一樣出校門上父親的車回家,我嘴裡哼哼唱唱,父親說:「別唱了,奶奶走了。」那種深沉的悲哀,是壓得人連一口氣都喘不上來的。在兩岸尚未開放往來時我曾隨父母到香港與兩位姑姑會面,令我驚訝的是,兩位姑姑不獨是與我父親生離了幾十年,她們彼此因為一在安徽一在貴州也是多年沒見過了。短短幾日的會親,說一頓哭一場,當又到了生離的關口,人人紅著眼眶,不知道再相逢是何年月日。事實上我的大姑姑前幾日故去了,那次香港之會就是她與我父親今生的最後一面,姑姑故去的事因我父親現在在病中還不敢讓他知道。我的母親當年自江蘇到台灣,情況比我父親好,除了我大舅舅之外,舉家都到了台灣。可就是這與大舅再見一面的希望,也在大舅病危、我母親與二舅飛機票都訂好了的情況下落空,終究沒來得及。所謂抱持希望,背後的涵義是沒有把握。沒有把握,正是人生中最大的折磨。離別真是再聚的開始嗎?
回想自身這前半生的經歷,我想我可說自己打小是個挺重感情的人。我六歲時與母親從香港到台灣,頭一年父親帶兄姐在港,第二年父親抵台,兄姐則各寄在香港的長輩家。我年紀雖小,對與家人分離卻是感觸很深的。我清楚記得盼望暑假快到能與兄姐相見,用一包話梅和一大盒口香糖作為數日子的依據,早早從月曆上算出還有多少天,規定自己隔多少天才能吃一顆話梅或口香糖;還常常故意忍住不吃,好在某一天可以一連吃上幾顆,讓自己感覺日子過得快些。稟著這樣的天性,我在成長之後面臨生離,更是格外傷情。小時候的那段分離還是有日子可數的,盼得到頭的,到了如今這歲數,面對的情況往往是看不到底的。死別的經驗多了之後,人會變得敏感,深恐哪一次的生離後再聚遙遙無期,竟會變成死別的前奏。以這十多年來說,多次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往返,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淚灑機艙的紀錄。最嚴重的一回從北京哭到香港,換了飛機再接著從香港哭回台灣,一分鐘眼淚都沒停過。生離最磨人處,在寄望於虛無縹緲,在計畫趕不上變化,在心頭無盡無休的牽掛,更在手中空無籌碼。
如果生離與死別可以選擇,我選後者。生離徒然肝腸痛壞,死別尚給幾許痛快。
![]()
∼嘆世間 月圓容易人圓難
於2004/09/28中秋夜
回龍女心聲